焚香:启智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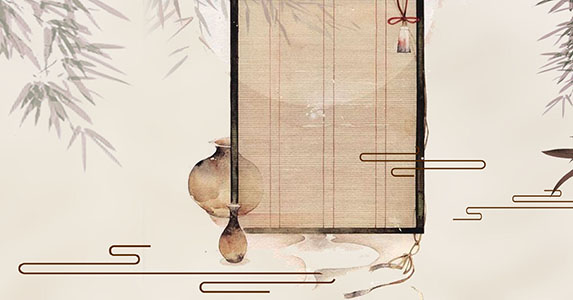
1.交易
青袍利落的英气女子跪坐在菀笙面前,微笑,“敢问姑娘可有提升人智慧的香?”
身披羽衣,发间赤红璎珞微微摇动的少女细细打量着她,笑:“有倒是有,不过姑娘肯出什么价呢?”
司枕烟思索了下,抚着面颊提议:“我银子很少,不过,拿容貌换如何?”见菀笙愕然,她挺了挺腰杆,极自信地循循善诱,“我虽算不上绝美,但比起宫中美人,也不遑多让。姑娘并不吃亏。”
菀笙失笑,这般自信又不看重容貌的女子,真的不多了,倒也算有个性。既如此,倒不如成全她。
菀笙列出三个名字,“诸葛孔明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;张子房,事了拂衣去,深藏功与名;司马仲达,多智近妖,反客为主。姑娘心仪哪种?”
司枕烟盯着三个名字,陷入了沉思。
司枕烟遇到靳咏的时候,才七岁。那年北狄铁蹄踏进大同,全城逃难,无论男女老少,无论贫寒富贵。
司枕烟的父亲是县令,守城不利,除了以身殉城,别无他法。
年幼的女孩跟着逃难大军走走停停,质料上乘的衣裙破损不堪。乳母为了自家女儿,抛弃了她,拿着司县令备下的盘缠跑了,只给司枕烟留下了两张烙饼,一把碎银。
那时节,银子能干什么呢?两张饼最起码能让她两天不饿肚子,银子却买不来食物,反而容易让人觊觎。
第三天,司枕烟混进了一户人家的队伍,人家看她年纪小,也没赶她。
第五天的时候,大半难民食物耗尽,饥饿催逼着他们暴动,抢空了靳家的私藏。司枕烟再没了食物来源。饿急的时候,她学着大人,将路边的草根挖出来咀嚼。
第七天晚上,那户人家的管家不知从哪里讨来了半块干馍,偷摸塞给自家少爷。靳咏接过馍只看了一眼,就顺手递给了司枕烟。女孩子受宠若惊,诧异问他:“你不吃么?”
靳咏嘴唇干裂,稍微一抿,血珠就涌了出来,显然也是饥渴得厉害。尽管如此,八岁男孩依然冷着脸,摇了摇头。
司枕烟也是饿得狠了,不敢确定第二遍,狼吞虎咽吃下了馍。
天快亮的时候,靳咏晕倒了,饿得。司枕烟后悔得直想剖开肚子,把馍还给他。
幸好,靳家的分支赶到了,匆匆给靳咏灌了碗米汤,才抢回了一条命。
后来,司枕烟作为义妹,跟着靳咏去了青州分支家。说是义妹,其实靳家人一直将她视作高等侍女。她不在意名分,娇生惯养的姑娘去学了武,只因为她永远记得难民暴动时,靳家的无助,记得靳咏将唯一的馍留给了她。
只是,和平时期,钟鸣鼎食之家的少爷,身边扈从如云,却很少需要她保护了。
司枕烟不想做个废物,她觉得,她承受了靳咏太多恩惠,总要有所作用。
青州的分家并不安分,靳咏的父亲与大同城共存亡,给幼子留下了百年世家偌大家财。青州分家在大同收复后,就以靳咏的名义接收了大半家产,又说他年幼,怕恶奴欺主,将他留在了青州。如今,靳咏十七,青州分家却已经将四成产业的管事撤换成了自己人,明显是不想还了。
靳咏曾冷笑着对司枕烟道:“若不是几位先生也跟着来了,只怕我早就被他们养废了!”
只是,司枕烟并不聪明,否则当年也不会被乳母坑得一无所有。她深感学武无用,反而智谋才是靳咏急需的。
此时思索着三个名字,司枕烟下了决心,扬眉笑道:“我选诸葛孔明。我欠他一条命和九年安康,就算鞠躬尽瘁,也只是扯平了。”
菀笙沉默半晌,劝她:“孔明一辈子太过辛苦,为了知遇之恩,耗干了自己心血,幼主却未必领情。说起来,还是张子房活得潇洒,也符合姑娘性情……”
“不!”司枕烟抬眼看她,“我并不觉得辛苦。只怕心苦。”
菀笙微微失神,当年的师姐,为了商君也这般飞蛾扑火。只是姑娘,你究竟是为了报恩,还是为了男女之情?
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罢!
菀笙将四枚香篆放在她面前,解释道:“你每用一枚,智慧就开启一分,容貌则会减少一分。四枚过后,你这张脸顶多只能算作清秀,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。该如何权衡,你可想好了?”
“多谢。”司枕烟根本不做考虑,一把将香篆全接了过来。容貌算什么?天下美人何其多,也没见对靳哥哥有用。
2.对决
菀笙指导着司枕烟用了一枚启智香,熏香袅袅中,无数纷杂的世事涌入脑海,百会穴似乎被一股温泉冲开,新鲜的空气,智者的呢喃,轻轻将她环绕。
这种感觉直到两刻钟后,才慢慢消散。
司枕烟耳聪目明,往日被人算计而不自知的关窍忽然想通了,曾经为之束手的难事忽然就有了应对之法。同样,她的面容失却了一分魅力,妙目横睇间,再没了让人怦然心动的感觉。
“多谢姑娘。”司枕烟一抱拳,匆匆离开了客栈。
“又是一个傻子。”菀笙叹息着退了房,向城外走去。至于结果,与她无关,她只负责收酬劳办事,不会平白付出。得来太容易的东西,世人总不知珍惜。
司枕烟回到靳家的时候,族老们正在议事。在靳咏反复要求下,青州分家同意暂时将两个商铺交给他打理,年底视情况决定由他接管多少生意。
青州分家的家主靳相仍然不肯放弃,殷殷劝说:“少主您将来是要出仕的,怎能沾染铜臭呢?不如安心读书……”
“我阿兄身份尊贵,自然不会亲手打理。但我却是略懂。”清越的女声响彻花厅,司枕烟径自走到靳相面前,拿起账册翻了几翻,盈盈笑道,“哎呀,相叔叔真是用心良苦啊!这两家常年亏损,要您贴补银子才能撑下去,您却给了我阿兄,还相信阿兄能扭转盈亏。相叔叔,真是感谢您对阿兄的信任哦!”
靳相被当众揭穿了目的,羞恼不已,可又不能跟个小姑娘计较,只能瞪靳咏,“少主,这是咱们靳家议事,外人不好参与吧?”
靳咏头一次发现,当年捡来的小姑娘竟是这般自信夺目。闻言,他轻轻一笑,“相叔叔没听她唤我阿兄么?”说罢,也不管靳相的脸色,冲那摞账簿一扬下巴,极自然地吩咐,“枕烟,挑两家。这就是咱们今年的任务了。”
司枕烟自是不会放过这种纵览全局的机会,她当场拿起账簿,飞速翻阅。半天后,她闭目沉思,心中冷笑,这个靳相,果然是不愿归还家产,钟鸣鼎食之家,收支未免太小家子气了!
她似笑非笑瞟向靳相,啧啧,“我看相叔叔指的那两家就很好。这人呢,重要的是听话,其次才是本事。我阿兄脾气不好,只留听话的,免得到时起了冲突大家都不好看。相叔叔,多担待。”
靳相见她选了那两家亏损的,本来还欣喜,待听出她这是要人事权,脸色就不大好看了。可当着各分家家主的面儿,又不能拒绝,只能干巴巴道:“少主只挑顺眼的就好。”
司枕烟打蛇随棍上,一指抱账簿的年轻人,笑道:“哎,这人长得挺顺眼,正好做个跑堂。”
年轻人倒是个有决断的,闻言立即下拜,“牛宝谢姑娘赏识,日后必唯少主马首是瞻!”
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众人散去后,靳咏笑看司枕烟,“你今日气度,倒是与以往不同。”
司枕烟脸皮一热,讷讷,“大约是开窍了吧!”
靳咏本想摸摸她的脑袋,但手举至头顶,忽然一愣,这才发现这女孩长大了,不再是以前跟在自己身后撒娇的女童了。他莫名有种失落自豪混杂的情绪。半晌,他有些生硬地问:“那么多家商铺,怎么选了这两家亏损的?”
司枕烟笑,“扭亏为盈,强势打脸,这戏不好么?”见靳咏不赞同地皱眉,她解释道,“这两家其实地段挺好,顾客也挺多,但就是一直亏。我在酒肆茶楼听人说起,商铺东西不太好,而且管事是相家主妾室的哥哥。”
“贪墨?”靳咏恍然,“堂堂靳家自不会以次充好,可这位管事就……难怪你要把人事权抓手里。那牛宝又是怎么回事?”
司枕烟眨眨眼,恭喜道:“这您可捡到宝了!刚刚我翻账簿的时候,牛宝一直小声告诉我哪页哪行有问题。十几本账簿啊,他居然记得一清二楚,可见对靳家的生意是熟悉到骨子里了。”
靳咏低头看着侃侃而谈的少女,以前作为花瓶固然很美,可如今这种自信飞扬的神态更让他心动。
司枕烟被他看得羞涩,讷讷提醒:“靳哥哥,你是不是该跟牛宝谈谈?”
靳咏醒悟,转身离去,走到抄手游廊边,忽然又转头对她笑,“枕烟,你,很不错。有女主人的风范。”
司枕烟蓦然涨红了脸,他们之间似乎有什么东西戳破了。
3.故人
司枕烟在牛宝的协助下,大刀阔斧对两家商铺进行了整改。桂花飘香的时候,两家商铺的收益已经一跃成为青州所有商铺的收入之首。
靳相尽管不甘,但在众分家家主虎视眈眈之下,还是不得不提前吐出了一些盈利少的产业。
“咱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接下来,就该合纵连横,挑选盟友夺取权力了。”这半年来,司枕烟的容貌又黯淡了一分,但她却成功为靳咏成立了情报机构。
靳咏失神地看着她,将各色补品推到她面前,劝道:“瞧你,都累得憔悴了,肌肤也没原先好了。女孩子家,要保养好才行啊!”
指点江山的司枕烟一愣,而后苦笑,她的容颜不是累的,也养不回来了。从她与菀笙达成交易那刻起,她就放弃了自己容貌。
司枕烟很忙,忙着收拢靳家祖业,忙着联络盟友,忙着为靳咏打通科举的关窍。当又一次与牛宝在书房凑合半夜后,靳咏冷着脸将她强拖到厨房,帮她打了热水让她洗脸,又让人端了粥过来。
老管家悄悄告诉她,今天是靳咏的生辰,他谁也没邀,只让人准备了家常菜,打算跟司枕烟一起过。
司枕烟很内疚,讷讷不知该怎么道歉。
送她回房的路上,靳咏折了枝带雪的寒梅,忽而吟道: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枕烟,六一居士也有首关于黄昏的诗。”
靳咏眼眸含笑,灼灼望着司枕烟。她低垂了螓首,红晕漫上脖颈,声若蚊蚋,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”她横了靳咏一眼,啐道,“你明知道是什么,却偏要我来说!”
靳咏笑着拥她入怀,司枕烟没有拒绝,柔柔伏在他肩头,任他收紧了双臂。
靳咏深吸一口气,呢喃:“枕烟,嫁给我吧?”
司枕烟泪水夺眶而出,她曾经以为自己与靳咏只是兄妹之情,如今能走到这步,竟让她生出了恍如隔世的错觉。
两人的感情提上日程后,靳咏仗着没直系长辈管束,强硬地定下了婚事,并且开始找寻司枕烟的亲属。
这日,靳咏带着一个姑娘兴冲冲跑来找她,“枕烟,你看我找到谁了!你妹妹哎!”
妹妹?
司枕烟愕然,她是独生女,哪里来的妹妹?
粉白襦裙的女孩子,俏生生站在花丛里,当真安静美好。
司枕烟眯眼打量着司念,目光顿在她发间缠枝桃花金簪上,精致的簪子,带着岁月的痕迹,那是父亲送给母亲的,后来逃难时被乳母卷走。看这年岁,女子应与自己年龄相仿,那么她是谁,也就呼之欲出了。
司枕烟眸中露出轻视的神色,冷笑,“不巧,家父只我一女,再无其他子女。姑娘大约是认错门了吧?”
司念愕然抬头,她的养父要她来道贺,只说是她亲人,却没告诉她是谁。如今被这番抢白,再细细一打量,她忽然削肩颤抖,泫然泣道:“姐姐,你是姐姐?我知你还怪着当年咱们走散,令你独自逃难。可姐姐那时脾气大,我娘亲身份卑微,您要去哪里,我们如何劝得住……”
靳咏一怔,心中打了个突,惊喜变惊吓了?
司枕烟拂袖不悦,“王念,我给你留了面子,你的母亲,我的乳母,当年做了什么,你清楚,我也清楚。你有父有母,请不要玷污我司家门楣!”
司念哭得更狠,反反复复念叨:“当年大夫人容不下我娘,姐姐如今也容不下我么?”
司枕烟脾气本就不好,这一年智谋长了,却还是快意恩仇的性子,哪能容她这般,当即就要将她打将出去,却被靳咏给拦了下来。司枕烟疑惑看他,靳咏含糊道:“她,是陈藩台的养女。”
“她?”司枕烟气笑了,一个乳母之女,一个席卷她所有盘缠的人,如今还攀上高枝了?
靳咏安排司念住下后,才无奈地告诉司枕烟,当年乳母抛下司枕烟不久,就被一众恶徒盯上了,他们抢走了那些财物,奸杀了乳母。正巧当时赶去救援大同的陈藩台路过,救下了司念,一眼就认出了那支缠枝桃花金簪,询问她与司县令是何关系。
司念当时哭得梨花带雨,自称是司县令之女,陈藩台却不信,故意板了脸唬她。司念只好告诉他,自己是庶出,因司夫人容不下旁人,娘亲才做了司家的乳母。
陈藩台哪里能想到七岁大的女娃娃能有这番心计,只当这才是实话,自忖与司县令有同年之谊,既是故人之女,不妨养在膝下,也算是尽了心意。
后来陈藩台因救援大同有功,一路升迁做了藩台,司念也就跟着成了藩台府的小娘子,读书习字,逢迎贵人,一样不缺。
4.并蒂
司枕烟很愤怒,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,“让她走!我亲自给陈藩台写信,我爹只我娘一个妻,这种满嘴谎言的女子,不能留着!”
靳咏的态度却让人难以捉摸,他道:“你那时才多大,大人的事,自然要瞒着你。”
“你不信我?”司枕烟愤然掀桌,“我告诉你,有她没我,有我没她,你自己选吧!”
司枕烟摔门而去,靳咏脸色很是难堪。到底谁才是靳家的主人?
“靳公子。”司念柔弱站在门边,面上垂下两行清泪,“我只有姐姐这一个亲人了,她却不肯认我,我还是回大同吧!”
“别急,她只是一时不能接受。”靳咏叹了口气,收敛了怒气,起身宽慰她,“你先住下,我再劝劝,总会让你们姐妹相认。”
“姐夫……”司念极尽哀婉地唤了一声,委屈,“养父家从来没人这般疾言厉色。这么多年了,姐姐脾气半点没变。”
靳咏有些尴尬,看看被摔得有些破损的门,不由扶额。
翌日见司枕烟的时候,她依然冷着脸。靳咏负手过去,说话有些漫无边际,“如今跟青州分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,我打算迁回大同。”顿了顿,他又道,“而且,大同那边,科举好考一些。”
司枕烟霍然转头,她听懂了,靳咏在劝她息事宁人,认下司念这个妹妹,这样算是跟藩台府有了桥梁。她心中有些不舒服,生硬地道:“陈藩台是看在父亲的份上才认她做养女。若我跟他说清楚……”
“藩台府就没脸了。”靳咏截断她,无奈,“枕烟,我以为你很聪明。”
司枕烟强忍住酸涩,她是聪明了很多,但本质上她还是那个爱恨分明的女孩。靳咏这种做法,让她有些难以接受。
“你若不愿跟她打交道,就交给我吧!”靳咏扶住她的肩,叹气,“不过是个小姑娘,你攥着她的命脉,她也不敢放肆。与其跟她撕破脸,倒不如让她替咱们办事。”
司枕烟张了张嘴,还是没能说出拒绝的话。
司念来靳府不过几日,就得了很多人的欣赏。靳相更是怂恿了自己儿子追求她。
这日,靳咏正在书房读书,门忽然被撞了开来。司念一头薄汗,尴尬笑笑,“姐夫在啊,那个,我去别地儿躲躲。”
“怎么回事?”靳咏急忙叫住她。
司念十分委屈,“相叔叔的公子,一直找我。可养父不许人家跟商人之子来往,说要找也得找读书人。我抹不开面子拒绝,只好躲了。”
靳咏沉了脸,他这还在青州,靳相就上赶着挖墙脚来了?
此事一出,靳咏更坚定了迁回大同的心思。
司枕烟看出他的意思,提前做了准备。琐事太多,她忙不过来,只好又烧了枚香篆。
靳相的儿子再没来找过司念,据说是在花园睡觉中了风。
从青州启程那天,靳咏看看司枕烟,再看看司念,微微失神,总觉得司枕烟没有司念好看了。他琢磨了下,得出了一个令他唾弃自己的结论——情人眼里出西施。
一路上,司枕烟忙着安排车队,跟各分家主事会面,有时候两三天都见不到靳咏一面。
孤男寡女,共处一路的结果就是,进大同城的时候,靳咏跟司念好上了。
司念抢先去求了陈藩台,陈藩台和靳家族老又找了大儒保媒,直到一切尘埃落定,才告知司枕烟。
司枕烟手脚冰凉,质问陈藩台:“您早就知道我与靳哥哥青梅竹马,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,说嫁就嫁?我堂堂司家嫡女,被您置于何处?”
“放肆!”陈藩台恼怒,冷笑,“若说身份不明,念儿最起码还有金簪为证,你有什么能证明自己是司家嫡女的?”
“当初乳母把我的东西都卷走了……”
“你怎么不说自己当初脾气大?逃难还非要穿华丽衣服,说你几句就负气出走?”陈藩台很失望,这个故人嫡女,比起司念,实在太不懂事了。
他淡淡交代:“司念虽说是庶出,但毕竟长在我膝下,没有作妾的道理。倒是你,收敛一下你这脾气,是不是司家嫡女,还两说。”
司枕烟气得肺疼,当场拂袖离去。
“爹爹。”司念一俟司枕烟离开,就红着眼圈从屏风后转了出来,“姐姐虽说相貌变了太多,可这脾气倒是与当年一般无二,想来,是不会错的吧?”
陈藩台淡淡瞟她一眼,冷哼:“当年司家夫妇都非中人之姿,可司枕烟的相貌未免过于平庸。你这孩子,就是太好说话,被人欺负到头上了,还这般软弱。靳家家大业大,为父若不给你争来这正妻之位,以后有的受了。”
5.婚变
司枕烟与靳咏大吵了一架,虽说靳咏反复保证会一视同仁,但还是让她心凉。
她至今都不知道,为什么当初夸她利落豪气的人,如今都在指责她仗势欺人。
正巧靳家重新接收大同的祖业出了岔子,司枕烟觉得,趁此机会分开一下也好。她带着牛宝等人前往出事的地方,跟劫镖的劫匪谈判。耗了几天,物资没拿回来,劫匪反而看上了她,被她收拾了一通才老实。
司枕烟越发觉得容貌这东西不中用,还不如多加点智慧坑死这帮劫匪。于是,她燃烧了最后一枚香篆。
她成功带着劫匪尸首与物资回城那天,靳咏正好娶司念过门。
浩大的婚礼刺痛了她的眼,那些艳丽的红色刺激得她想杀人。牛宝一把按住她,急急劝道:“冷静!姑娘,她身后有陈藩台。”
司枕烟深吸一口气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既然到了这份上,她也没必要再在靳咏身上耗了。即便诸葛孔明鞠躬尽瘁,可他最起码没有一个背后捅刀子的主子。她如今只想在不搭上自己的情况下,出了这口恶气。
一对忘恩负义的母女,真当她虎落平阳,能被犬欺了?
新人拜堂的时候,司枕烟潜入到了人群,悄悄向靳相耳语一番。靳相登时勃然大怒,推开众人,戟指着司念大喝:“贱人,把你的簪子拔下来!”
一室俱静,半晌,坐在首座的陈藩台才怒道:“你做什么?”
靳相死死盯着司念冷笑,“我儿即便追求过你,也甚守礼节,你若不愿,拒绝便是,又何必以毒针伤人?还是说,你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了犬子手里?”
司念愕然,连忙摇头,“我不懂您的意思。”
靳相一指那支缠枝桃花金簪,冷哼,“那簪子里有毒针,应当跟我儿中的毒是一样的。”
陈藩台将信将疑,拧开了簪子,果然在其中发现了毒针。司念全身骤然发冷,这簪子是母亲当年卷走的,作为司家信物,她甚是爱惜,自是不知还能拧开。她骤然转头,死死盯着司枕烟,怨毒大喝:“是你,是你干的!”
司枕烟抱臂嗤笑,“进城没多久,我就走了。你这簪子整天寸步不离,我上哪儿安排这出?”
众宾客哗然,看向司念的眼神立马不一样了。
陈藩台脸色难看,沉声喝问:“毒针有些年头了,这般危险的东西,你父母没交代过你么?”
“我……”司念如坠冰窖,她知道,不管靳相的儿子是不是她伤的,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,陈藩台再不信她是司家人了。
后记
靳家的婚事告吹了,新娘子因陈藩台求情,只是被赶出了大同,没有入狱。也因为此事,陈藩台自感识人不明,向朝廷乞骸骨。
司枕烟将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下去,准备彻底放手了。
临走那晚,她向靳咏辞行。
“你等等。”靳咏换下吉服,脸色苍白而疲倦,他轻轻请求,“一起喝一杯吧!”
司枕烟本想说,三更半夜,孤男寡女,不合适。可是一触及对方哀伤的眼神,她就心软了,犹豫了下,点点头。
司枕烟悲哀地发现,即便她自诩潇洒,对待靳咏却始终存了一丝软弱。
庭院深深,靳咏的眸子跟夜色一样深沉。他亲自斟酒布菜,眼里有司枕烟看不懂的东西。
“枕烟,”他幽幽叹息,“能不走么?”
一杯酒饮尽,司枕烟笑睇他,“留下来?以什么身份呢?”
靳咏张了张嘴,他想说,我的妻。
可是,婚宴的峥嵘横亘在二人之间,如楚河汉界,愈发清晰。
“醒醒吧,靳咏。”司枕烟连名带姓唤他,“该你的,欠你的,我早已还清。你既已背叛了我们的曾经,我怎么可能还继续傻傻等你回头?”
她站起来,强忍住哽咽,一字一顿说:“我司枕烟,从来都不是能和别人共享夫君之人。”
靳咏倏地攥紧了酒杯,怆然而笑,他喃喃道:“走不了,你走不了的……”
“什么?”司枕烟疑惑侧头,却觉天旋地转,身体无力地倒下。
半刻钟后,她才知靳咏带来的是让人长期昏迷的毒酒,乃是从那枚毒针中萃取的。
意识昏沉中,靳咏抚上她的脸,叹息,“是你伤的人吧?你想从靳相手里夺权?是为了我,对不对?傻子。”他拥她入怀,陶醉般地呢喃,“我不会再放你离开了。你是我的。”
他与她,从陌路相逢,到相互扶持,他以为,那是永久,却原来她还是会走的,在自己伤她一次又一次后。
可是,怎么可以呢?
她怎么能走呢?
犹如筷子,得是一对儿才有意义。她是他的,他也是她的,他们谁也离不开谁。
靳咏看着神色挣扎的司枕烟,不期然想起了往事。他永远也不会告诉司枕烟,当初那块馍,他是嫌弃干硬不想吃。
半块干馍,就换来了司枕烟一世。